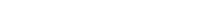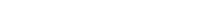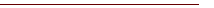|
嘉樹新苗 現代中國水墨畫展 |
|||||||
|
幽靈和新現實──國畫和文化自性 2,000 年近在眉睫之時,在亞洲,在西方,人們開始注目近當代中國藝術起來了。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英國統治之後,終於又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和旅居海外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在亞洲、歐洲和美國展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美術館翻整一新,於近期重新開放。安思遠 (Robert H. Ellsworth) 慷慨捐贈的大批 19 、 20 世紀中國繪畫作品與早期的中國繪畫同時展出,轟動一時。 Solomon R. Guggenheim 博物館正在籌劃中華藝術五千年大型展覽,其中將包括各種風格的近當代作品: Asia Society 也正在組織海外華人藝術家的現代藝術作品,預計在 1998 年秋季展出。 在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正在籌備一次宏大的展覽,並冠之以一個宏大的名稱: ”'97 世界中國書法繪畫展 ” 。這次展覽主要收集世界各地中國藝術家的傳統作品,在中國幾大城市及美國、加拿大巡迴展出。 在當下的藝術品市場上,傳統風格和西方風格的當代中國畫行情看好。中國的許多城市以及紐約、香港、臺北、新加坡都定期舉辦現代中國畫拍賣會。世界各地相繼建立了現代中國畫畫廊,一些經營中國古代藝術品的經紀人(包括懷古堂)也開始兼營現代作品。 我們一下子掉進了 20 世紀中國藝術的汪洋大海。在我們評價這些藝術作品的藝術和藝術史價值之前,最好先簡略地回顧一下過去一個世紀裡中國藝術界的大事和風格變化,這是這一階段藝術創造的環境。 在過去一百年中,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發生了空前的巨變。統治中國千年的皇帝是 1911 年被徹底推翻的,然而在此之前,中國人對其傳統和價值的反思以及對其文化自性的環境,比這還要早一些。 Julia Andrews 最近在研究共和國藝術時作了這樣的總結 : “ 19 世紀末晚清 (1644-1911)" 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國際社會是由領導現代技術的西方和日本統治著。在軍事上,中國 1842 年和 1860 年敗於英國, 1885 年敗於法國, 1895 年敗於日本, 1900 年又敗於八國聯軍,這些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中國已無法在世界上保持其應有的地位。 20 世紀最初幾十年,中國思想界所有的爭論都圍繞著同一個話題,即中國應該如何渡過危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落後也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因此中國根本不可能在現代世界中發揮任何作用,另一些人提出修正中國文化,使中國成為生龍活虎的現代力量。更有一些人相信中國文化有其獨特的價值,必須不遺餘力地加以保護。 " [l] 這時,視覺藝術界也在談論著同樣的話題。傳統中國畫(國畫) [2] 尤其是宋朝以後的國畫,受到批評。批評者認為國畫缺乏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精神,畫家對當代社會的殘酷現實視而不見,卻津律樂道子虛烏有的儒家理想社會。文人畫更是倍受抨擊,抨擊之最烈者莫過於主張改良的康有為 (1858-1927) 。他說:“故以畫論,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國幾佔第一位矣。情後不長進耳……。 "( 以上引《歐洲十一國遊記》 ) “今工商百業皆藉於畫,畫不改進,工商無可言……。 " “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蓋由畫論之謬也 . ……。 ” ,“而謂士夫游藝之餘,能盡萬物之性歟?必不可得矣,然則專貴士氣?為畫意正宗?豈不謬哉?, [3] (以上引《萬木草堂藏中國畫目》)。 康有為道出了一代進步知識分子的觀點,他們相信現代化即西化,西化即發展科學和技術。這些進步的觀念成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主要思潮至少有數十年之多。幾年之後,北京大學校長, 1919 年五四運動領導人之一蔡元培指出:“蓋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的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至於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之進步而進步。 "[4] 追求進步,並且認為西方藝術(中國人眼中的西方藝術)先天就更科學更現代(因而更好),這給文人畫的倡導者出了一道難題,而且幾乎斷送了國畫傳統。 許多藝術家沒有完全放棄傳統的中國畫,而是嘗試著在主題或風格上作些調整,使國畫的路于走得更寬,風格更現代,使之適應當代社會的需求。中國畫的“白話運動 " (借用一個文學名詞,然而文學中的口語化運動遠比美術界來得深遠)集中體現在偉大的畫家齊白石 (1864-1955) 的作品中,他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物件畫得活靈活現,在傳統中引入了耳熟能詳的口語化語匯,使傳統重新充滿了活力。然而,齊白石並沒有拋棄考究的筆法、簡潔的形象和直接的表達等等傳統的美學價值 ; 相反,他的作品將這些特徵發揚光大。齊白石的風格為其後 50 年的國畫奠定了基礎,這是齊白石最大的成功。 包括康有為在內的大多數批評家主張藝術上的中西合璧:“若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國人豈無英絕之士,應運而興,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者,其在今乎,吾斯望之。 "[5] 康有為這樣說?因為他認為他和其他參加 1898 年失敗的改良運動的“自強者 " ,為中國大多數的弊病指出了一條療救之路。 Jonathan Spence 對此作了如正解釋 :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通常簡稱為「體用」,在一個面臨痛苦巨變的時代,這在文化上不失為一個穩妥的立場。它肯定了使中國文化延續並賦予它意義的道德和哲學價值的基礎結構。只要有這樣的信念,中國就能迅速奉行各式各樣西方之事,師西方之人。“[6] 本世紀初,一批年輕畫家熱切地嚮應了康有為的號召。有些人,如傅抱石 (1904-1965) 和高氏兄弟 ( 嶺南畫派的創建者 ) ,東渡日本路,去考察日本藝術家如何有選擇地吸收西方的技巧和風格,使其民族傳統現代化。另一些更負盛名的畫家,如徐悲鴻 (1895-1953) 、劉海栗 (1896-1994) 和林風眠 (1900-1991) ,到歐洲去親歷西方文化的熏染,盡力學習歐洲藝術。 中國畫需要融合西方藝術的技巧以進入現代,在這一點上眾人並無異議,然而西化運動的三位領袖,徐悲鴻、劉海果和林風眠,在其它方面卻各持己見。徐悲鴻推崇現實主義的學院派油畫。以在其畫院率先使用裸體模特兒而聞名的劉海栗心儀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畫家。而林風眠則對 Matisse 和 Vlaminck 情有獨鐘。 三個人在應該學習外國的哪一個派別上相持不下,很像當時的國畫家常為應該模仿“四王 " (如吳湖帆及其弟子)還是石濤和八大山人(如張大千和他的追隨者)爭論不休。歷史可以證明,徐悲鴻的學院派現實主義至少在短期內佔了上風,盡管這更多是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原因,而不是藝術上的原因。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偉大的創作和藝術試驗的時期。隨著對西方和日本的日益開放、中國藝術家常常把些新奇的形式、技術和思想、生搬硬套過來,卻對其產生的文化背景不甚了了,正如著名作家魯迅在 1928 年所嘲諷的那樣: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涵義,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準作詩,是古典主義; 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著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7] 到三十年代末,中國藝術盡管有些混亂,但前景頗為樂觀,藝術家可以自由使用各種手段,他們便以巨大的熱情和奉獻精神,創作了各種風格的作品。傳統的繪畫後繼有人,西式的油畫和水彩畫也不斷出現,還出現了各種手段的使用,或基之以中國之“體”聯西方之“用 " 。然而,此後幾十年內,中國藝術家便陷於“共產主義 " 、“馬克思主義 " 和“毛澤東思想 " 的囹圄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創作、展覽、出版或本應廣泛傳播的藝術在各方面統統政治化了。這方面的研究近期有一些,將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有。 [8] 雖然許多問題還有待商榷,許多個案仍需重新考慮,但傳統中國畫顯然在中國大陸 50 至 80 年代的文藝政策中受到嚴重創傷。 Julia Andrews 在 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一書的前言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藝術作了比較。 “最大的變化是現實主義繪畫的地位來了一個飛躍,繪畫的手段各種各樣,而以油彩和樹膠水彩為最常用。這個變化很惹眼。盡管早期藝術家也有人採用西方藝術風格,但 1949 年以前,西方風格是沒有根底的。此外,我認為在中國各層坎藝術教育中全面地有選擇地融入西方手段和風格,割斷了中國藝術與其傳統的聯系。 " 雖然畫家們依然用墨和顏料在宣紙上塗抹,依然將他們的作品被成傳統的掛軸,但他們的筆法、主題和風格己經在政府的命令下改變了,整個中國畫變得面目全非。特別是過去中國畫大師那微妙而充滿文化底蘊的筆法,在當代實踐中已經蕩然無存了。隨之而去的,是這種藝術過去引起觀畫者視覺和精神上的愉悅的關鍵因素。 "[9] 毛澤東在 1942 年《延安文藝萃談會上的講話》中清楚地指出,他認為藝術必須為人民服務,為藝術而藝術是不可能的。 50 年代,毛開始把他的諾言付諸實施,重塑整個的藝術教育和創作。現實主義的油畫,主要是吸收了越來越多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人物畫,成為中國美術的新貴。藝術成為國家的一種工具,並且淪落到服從宣傳需要的地位。中國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不僅與他們的傳統相隔離,並且與世界其它地方的藝術和科學發展相隔離。 心理學家 Lawrence LeShan 和物理學家 Henry Margenau 合寫了一本書,書名很有意思,叫《愛因斯坦的空間和梵谷的天空》。其中有這麼一段話,蔡元培如果看了,也許會首肯 : “……一個時期組織現實的方式發生變化,藝術和科學是其主要推動力,它們總是平行地前進,時而這個略微領先,箭頭直指新生事物,時而是那個。藝術對現實的理解發生變化時多科學對世界的描述也會景跟著改變;反之亦然。當封閉的中世紀向文藝復興敞開時;當布魯諾 (Bruno) 向人們解釋無限的涵義時;當科學不再局限於神學問題,而是由加利略 (Galileo) 等人發展為全方位的科學時,藝術助長了這種態度,並為這種態度所助長。 ”[l0] 但是,對下面的這段話,不知蔡元培們會作何感想 : “我們通常所說的,「現實」一詞有一個確定的、易懂的最終意義。在它虎視耽耽的注視下,新現象往往成了它掌中的獵物。這從我們的過去產生的狹隘定義,如今嚴重地阻礙著我們的進步。 每個人都生活在一種文化中,其取向和基本信念塑了他,深深扎根於他一輩子的個性中。當他進入另一種新文化,面臨不同的取向和基本信念時,兩種現實就在他內心發生衝突。即使他已經在新文化中作了有用的一分子,他早先的取向依然對他產生影響。 人是這樣,知識也是這樣。一種知識的源頭像幽靈一樣漂游在這種知識之中,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什麼是真,什麼是對,什麼有意義,什麼無意義簡而言之,什麼是現實的根本形態或基礎。當一種知識在發展中參雜了與老信念相抵觸的新材料,這種知識裡就產生了根本的衝突。在接受、組織和解決新材料與舊觀念和基本取向的衝突所引發的新問題的過程中,便有艱難困苦和激烈的鬥事。鬥事會引起混亂,同一學科中學習的人會因此缺少交流。今日的科學就正處於這樣的鬥事中。一部分基本觀念,我們組織經驗之方法的幽靈,與各種科學領域中出現的新材料發生了抵觸。 "[1l] LeShan 和 Margenau 所關心的,是物理學由於其與生俱來的局限,無法充分描述和解釋所有的現象,尤其是新的科學發現提示出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標準的牛頓物理學關於時間和空間的概念行不通了。不間的現實和多重真理無法僅僅通過物理的方法加以理解。在理解這些新現實時,藝術、靈學、道德和意識都有各自的用武之地。書中一大部分,主要正關於科學理論的──對大多數藝術專家來說如同天書一般難懂,但書中的觀點包含了兩個很重要的認識。 一是藝術家描繪什麼以及他們的作品如何被理解受制於產生作品的文化環境: “藝術家在探尋意義和價值,組織宇宙時,並非東拉西湊,隨心所欲。在一種文化發展的每一階段,它都受其可能性的限制,並由幾個因素所左右。首先,藝術家和科學家一樣,受他們的技術方法的限制。在顯微鏡尚未發明的時候,科學家無法研究細菌,藝術家也受到類似的限制…… 藝術家可得的可能性還受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觀點的限制。每種文化裡都有些永遠可能或無法理解的東西…… 深藏於文化中的交互性和現實結構,‘自然,和‘意識,之間不斷的反饋和更正,‘認識論的反饋 ' ,大約最清楚不過地表現在藝術家與社會的關係中。藝術家在他的文化世界圖景以及他所了解的藝術創造的界線內,從各種連貫的可能性中選擇一種現實結構,然後在這種結構中寫作、作曲或繪畫。社會挑選它所青睞的藝術家,然後這些藝術家的觀念成為塑造社會的因素。 "[l2]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藝術官僚企圖通過嚴格限制藝術家的創作社題和風格左右全社會對現實的認識,並通過嚴格控制各種方式的,批評破壞自然的反饋過程。 LeShan 和 Margenau 指出 : “顯而易見多社會給予科學多少自由,便也給予藝術多少自由,可見藝術是對組織現實的新方式的探尋;總的說來,兩者受控制的程度也基本相同。 " 在一種文化的任何階段,藝術和科學都會有一些常規和摸不得的老虎屁股。即使在今天的美國,如果有什麼人觸犯了這些規則,他們的作品便不會在畫廊展出,論文也不會在科學雜誌上發表。在另一些文化裡,這種控制比現在的西方社會要嚴格得多。觸犯科學或藝術上的常規,結果往往是坐牢、關瘋人院,甚至被從懸崖上扔下來的事。 "[l3] 關於當代中國繪畫的第二點認識,是藝術家和科學家接近目標的途徑是不同的,畫家要對一個形象有某種深刻的理解,才能將它變成一件藝術作品 : “當一位畫家所描繪的世界與生活的那個世界相左時──比如一位現代畫家要畫一幅中世紀宗教題材的圖畫他所探索和擴大的就不是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是另外一個世界。於是,這畫看起來就矯揉造作。他走的是科學家的道路,是科學之路而不是藝術之路。科學之路是探尋和建立感知現實──我們在身外所感知的事物,並描述它們,於是我們能學到新東西,然後改變自己。藝術之路是改變我們內心的東西,於是我們能用不同的方式感覺感知世界(和我們的內心世界)” [l4] 正因為這樣,早先人們將國畫技法和新的“革命 " 主題相結合的努力,才會大多付諸東流。在對藝術控制得最嚴格的時期(如一次次的反右運動)。藝術家不僅只能畫規定的主題,而且必須用規定的風格。在這樣的環境中,只有見風使舵的插圖畫家能夠作畫,無怪乎那個時期的宣傳畫從風格到功能都更像西方的廣告,一點不像美術作品。 在所有的藝術家中,傳統畫家最難跟上形式,使他們的技法滿足人民共和國的新需要。西方繪畫和中國繪畫顯然有著不同的根源和發展道路; 他們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的產物。這兩個世界在我們這個時代要走到一起,這並不奇怪,因為現在全球的交流只在一彈指間便能完成,這種跨文化交流中最出奇的,甚至是可笑的事情,是當代中國和西方的藝術家和觀眾看待對方文化的眼光。他們常常背道而馳。 康有為和蔡元培這樣的理論家想要以西方的模式使中國藝術現代化,可是徐悲鴻的學院現實主義到中國時,已經是保守,甚至過時的東西了。這種畫風在作過一些意識形態上的“改進 " 後,被共和國的壓制性政策確立為官方的藝術表現手段。沒有人理睬西方科學和藝術的發展;這也和傳統繪畫一樣,是個禁區, Andrews 寫道: “到 1979 年,只有少數幾位老畫家掌握有著嚴謹的技法要求的傳統繪畫了。傳統中國畫已經不復作為一種活的藝術傳統而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五、六十年代畫院和中央美術學院在各地的分院興起的使用中國畫手段的新方法。現代主義的火種在 30 年代末日本入侵時就已是風雨飄搖,最後終於被共產主義徹底撲滅了。 1949 年後,現實主義油畫全面進入中國畫界,這在 20 年代初是西方人想都不敢想的。他們要是知道中國藝術界滿懷熱情地保留、實踐並發展著西方已經檳棄了近一個世界的畫風,大概會同樣地吃驚。 "[l5] 西方藝術本身當然也經歷了革命,反映了科學發現和哲學感覺所帶來的關於現實的新概念,比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量子力學,粒子物理。中國藝術家剛剛掌握一種他們認為是摩登的繪畫風格,西方藝術家和批評家卻已經拋棄了這種風格和它所代表的那種文化結構,而西方藝術家如 Picasso, Paul K1ee, Mark Toby 及 Jackson Pollock 熱衷於非西方的藝術傳統,包括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時,中國人自己卻說這些東西要不得。歐美許多藝術家通過研究東方靈性和藝術(有時借助於迷幻藥)探索不同的關於現實的觀點,而這時,中國大陸的藝術家正因於馬克思主義教條,被一種網羅在歪曲的現實中的繪畫傳統束縛著。是臺灣和海外的中國畫家,如張大千( Zhang Daqian,1899-1983 )、王紀千( C.C. Wang, 1907- )、曾佑和( Tseng Yuho, 1925- )和王無邪( Wucius Wong, 1936- ),發現並把握了傳統中國畫與 20 世紀西方藝術,尤其是抽象畫,在精神上的聯系。 Jeffrey Wech1er 最近在一篇探討美國現代藝術中東西方交流的文章中指出 : “談到抽象派,人們便說 Jackson Pollock 、 Franz Kline 、 Robert Motherwell 、 Mark Rothko 和 Adolph Gottlieb 在技法、構圖和形式上先進、有創見多甚至是一種突破。然而對許多熟悉亞洲傳統藝術的人來說,這實在有些可笑,因為他們看到傳統亞洲藝術的許多形式和技法特點,正是現代美術的視覺因素的前身,或者至少是與之同時存在的。 "[l6] 生活在大陸之外的中國藝術家沒有受到毛澤東時期的那種束縛,有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藝術環境,他們在真正融合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繪畫風格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因此,國畫的未來就將建造在他們的作品之上。 這次畫展展出了活躍在中國、香港、臺灣和海外的新一代傳統國畫家的作品。當然,國畫只是中國美術的一個方面。今天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藝比過去幾十年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了。自二、三十年代以來,年輕的中國藝術家從未能像現在這樣廣泛地探索風格和理論上的目標。對當代中國的視覺藝術作一個準確的評價,需要考察空前豐富的繪畫手段,除了傳統形式的中國畫和書法以外,還有油彩、丙稀顏料、水彩、樹膠水彩、雕塑、木刻、陶瓷、紡織品、膠片、平面設計及裝置藝術品)。臺灣、香港和海外的藝術家當然有更多的選擇,他們在當代藝術實踐中已經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然而,將國畫作為中國藝術的一大派別考察其現狀是很有神益的,因為縮小考察的焦點會使我們對更大的藝術課題看得更清晰。 這一代的年輕藝術家成長和生活在一個政治現實向文化自性提出了不可迴避的問題的時代。養育他們的那方水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與中國歷史和傳統價值的關係。臺灣似乎保留了許多傳統價值。而在大陸,這些東西有很多已被拋棄,至少是被冷落了。香港和海外的中國人每天都面臨著自性這麼一個複雜的問題。然而,這些有著五花八門的背景的中國藝術家,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同一種手段,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眾多的選擇面前,他們自覺地用毛筆、墨汁在宣紙上揮洒,這至少表明了與中國傳統藝術的一種緊密聯系。不同的藝術家選擇國畫當然是出於不同的原因,在本世紀初就是這樣。有些人是要融入源遠流長的藝術傳統,以此肯定他們的文化自性。有些人選擇國畫可能主要是對共產主義政權下壓制性的藝術政策的反抗,公開否認他們與最近的過去的聯系。對另一些人來說 3 他們之選擇這種藝術形式,是由於這種傳統于段直接而敏感,它對微妙之處的表現是無與倫比的,這些藝術家不論抱著何種政治觀點,都以這種方式肯定他們的藝術自性。 八、九十年代是一個新的開端,即使對那些一直在從事傳統中國畫創作的人來說也是這樣。新一代的藝術家抖擻了精神,以新眼光看待這古老的傳統。也許他們沒有前人臨摹書畫作品深厚的功力,在技法上不那麼爐火純青,但他們也沒有什麼包袱,不用苦苦地守著中國的藝術遺產和過時的文化價值。國畫不必是表達中國文化自性的唯一手段,因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的一個事實,就是沒有任何一種特性,沒有任何一種傳統,能夠代表所有的中國人。然而,同樣清楚的是,無論怎麼壓制,傳統中國畫總是那麼充滿活力,與人們點點相關。大多數中西兼顧的中國畫家,到晚年都表現出對中國畫的偏好,徐悲鴻、林風眠、劉海栗、吳作人 (1908-1997) 、李可染 (1907-1989) 、潘天壽 (1897-1991) 和石魯 (1919-1982) 都是如此。對中國藝術家來說,用毛筆和墨汁作畫就像用筷子吃飯一樣自在。 有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0 年來,或者,推翻清朝近 90 年來,國畫到底有多少發展提出質疑,但是想想傳統中國畫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這些年來受到的嚴厲批評,想想目前這琳琅滿目可供人選擇的藝術手段,這種藝術形式能堅持下來,已經是一個奇蹟了。自康有為提出“合中西而為晝學新紀元 ” ,至今已有近百年了,一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說這一遠大理想尚未完全實現,但藝術和文化自性的根本問題已經空前明了地擺在我們面前了。說到底,在中國歷史上,一百年不過一瞬間而已。 中國藝術,尤其是國畫的巨變已經就在眼前了,然而,我們不可能準確地預言新美術的發展方向,因為我們的全球環境已經遠非康有為、蔡元培、徐悲鴻的時代可比了。西方在技術和世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經濟學家、政治家和商人越來越多地向亞洲尋找出路。大眾文化已經全球化,最大的公司已經國際化。全世界的青年人聽一樣的音樂,吃一種口昧的漢堡飽,穿一種品牌的運動鞋。在電腦世界裡,國界消失了,信息以閃電般的速度在大陸之間傳播。現代通訊和交通使所有的市場國際化,藝術市場也不例外。 在一個快速分享的信息的時代,在一個越來越國際化的大眾文化中, 21 世紀的油彩、丙稀顏料的藝術,或者更可能是尚未發明的數碼手段,肯定會有一種真正國際化的風格。中國藝術家無疑將在這個發展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跨文化的藝術交流或為家常便飯,隨時可得,藝術風格廣泛地交互影響,即使還殘存著些許國家或地區風格,這些特點辨認起來也非常困難了。全世界的藝術家,包括中國藝術家,將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多元文化大講壇上闡述他們對新的全球現實的認識。 這個多元文化的環境將接受共同的文化價值,但也承認文化差異,鼓勵、保護和發展傳統藝術形式。大眾文化變得更加全球化。因此更加單一,為某一文化或種族獨有的特徵也就變得格外醒目並有意義。各種文化不再互相衝突,反而互相融合,各種藝術傳統的純潔性就待以重新發現。傳統中國畫可以與以其它于段創作的作品並存,今天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它不會取代其它藝術形式,也不會被其它藝術形式取代。國畫將繼續存在並繁榮下去,因為它有時間抹不去的獨特的藝術品質 : 寓於表現的線條、簡潔的造型和純潔的精神。 這次集中了五十八位活躍在亞洲和西方的藝術家的作品的畫展,也許會成為日後衡量和評價藝術發展的基準,這些各個相異的風格和主題既代表了當代國畫的水平,又展示了值得今後探索的一些新路。
|
|